六一恰遇端午,去哪儿遛娃好?“游玩地图”上新
六一恰遇端午,去哪儿遛娃好?“游玩地图”上新
六一恰遇端午,去哪儿遛娃好?“游玩地图”上新在(zài)《作为方法的(de)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一书中,学者刘昭吟与建筑师(jiànzhùshī)张云斌从厦门集美嘉庚故里的历史与现实中,总结(zǒngjié)出了30条模式词条,包纳了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,也提炼了陈嘉庚百年前一手(yīshǒu)创建新型社区时,所期待建设的公共生活图景。他们提出了一些美化空间、让生活方式变得更自然(zìrán)的建议,也分享了自己在集美大社生活的第一手见闻。
第一财经:住在集美大社的生活状态(zhuàngtài)怎么样?会不会(búhuì)担忧那里网红化?
刘昭吟:陈嘉庚在上世纪50年代(niándài)就想象集美的产业是教育(jiàoyù)和(hé)旅游,所以他修建龙舟池、游泳池、植物园、集美公园、鳌园、校园花园等公共设施,供居民使用,也是希望集美成为好的文化风景区。改革开放以后,别的地方在把农地转成工业用地发展工业,集美的地早都拿来支持陈嘉庚建校了(le),没有地发展工业了,自然而然地往旅游发展。大社卖沙茶面的河北人告诉我,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龙舟池摆摊卖旅游小商品,游客出门(chūmén)一定会消费(xiāofèi),分分钟(fēnzhōng)成“万元户(wànyuánhù)”。所以大社发展旅游并不是最近的事,它发生得很早,随着时代改变业态。
 人们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面(diànmiàn),而且很(hěn)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(jìnlái)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(dàshè)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(shí)没有游客,这么(zhème)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都(dōu)(dōu)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(zhǐmài)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(yìqǐ)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(shāngyè)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主动的(de)(de)还是(háishì)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(xiànshí),就算要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(xiàngshì)一个当地人(dāngdìrén)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(zài)(xiànzài)才有(yǒu),上世纪(shìjì)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(zhù)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(kěyǐ)说,从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(xuécūn)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kàndào),校园总有(zǒngyǒu)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因为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(duōnián)来,大社一直就是(jiùshì)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(shìjì)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人们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面(diànmiàn),而且很(hěn)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(jìnlái)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(dàshè)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(shí)没有游客,这么(zhème)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都(dōu)(dōu)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(zhǐmài)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(yìqǐ)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(shāngyè)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主动的(de)(de)还是(háishì)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(xiànshí),就算要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(xiàngshì)一个当地人(dāngdìrén)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(zài)(xiànzài)才有(yǒu),上世纪(shìjì)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(zhù)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(kěyǐ)说,从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(xuécūn)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kàndào),校园总有(zǒngyǒu)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因为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(duōnián)来,大社一直就是(jiùshì)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(shìjì)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 现在大社的(de)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(nèi)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(fǎnér)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(de)(de)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(tuīcè)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(shǔyú)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(jiùxué)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(fúlì)照顾(zhàogù),以及,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(de)缘故,我住在大社,作为外来人并不(bù)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,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(mán)乐意侃大山。同(tóng)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(hūyōu)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(tíxǐng)我口述(kǒushù)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(húshuōbādào)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(zài)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(xiě)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时间对不上,就是(jiùshì)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(de)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(shènzhì)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(xiǎngtòu)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(dài)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(nàyàng):“这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会“好好收(shōu)起来”,有点啼笑皆非(tíxiàojiēfēi)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(yánjiū)的。
传统文化在(zài)现代冲击中延续
第一财经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(shāngyè)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(liúzhāoyín):大社(dàshè)的(de)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是(shì)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(quánshè)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,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(wàiqiān)较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(lèisì)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是渔民,都很(hěn)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(rénshù)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(yāoqǐng)集大体(dàtǐ)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(fāngshì)对(duì)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(wǎngwǎng)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(bùnéng)放炮,实在(shízài)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(de)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(biànchéng)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(yóu)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(zìjǐ)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跟上(shàng)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(méiyǒu)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现在大社的(de)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(nèi)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(fǎnér)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(de)(de)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(tuīcè)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(shǔyú)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(jiùxué)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(fúlì)照顾(zhàogù),以及,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(de)缘故,我住在大社,作为外来人并不(bù)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,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(mán)乐意侃大山。同(tóng)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(hūyōu)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(tíxǐng)我口述(kǒushù)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(húshuōbādào)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(zài)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(xiě)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时间对不上,就是(jiùshì)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(de)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(shènzhì)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(xiǎngtòu)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(dài)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(nàyàng):“这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会“好好收(shōu)起来”,有点啼笑皆非(tíxiàojiēfēi)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(yánjiū)的。
传统文化在(zài)现代冲击中延续
第一财经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(shāngyè)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(liúzhāoyín):大社(dàshè)的(de)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是(shì)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(quánshè)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,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(wàiqiān)较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(lèisì)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是渔民,都很(hěn)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(rénshù)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(yāoqǐng)集大体(dàtǐ)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(fāngshì)对(duì)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(wǎngwǎng)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(bùnéng)放炮,实在(shízài)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(de)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(biànchéng)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(yóu)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(zìjǐ)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跟上(shàng)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(méiyǒu)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 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(jīgòu)、小区、自建房(zìjiànfáng),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(zhàngliáng)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(jiūfēn)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围墙,仅仅退让1到(dào)2尺,就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
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(bùrěn)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南薰楼,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(chāichú)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,使(shǐ)南薰楼露出来(lái)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(shì)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
但是(shì)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(róngyì)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(jiǎng)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(niànzīzàizī)的公共性上。
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(jīgòu)、小区、自建房(zìjiànfáng),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(zhàngliáng)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(jiūfēn)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围墙,仅仅退让1到(dào)2尺,就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
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(bùrěn)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南薰楼,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(chāichú)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,使(shǐ)南薰楼露出来(lái)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(shì)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
但是(shì)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(róngyì)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(jiǎng)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(niànzīzàizī)的公共性上。
 《作为方法(fāngfǎ)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文化出版社(chūbǎnshè)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(láizì)第一财经)
《作为方法(fāngfǎ)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文化出版社(chūbǎnshè)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(láizì)第一财经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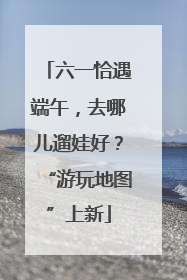
在(zài)《作为方法的(de)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一书中,学者刘昭吟与建筑师(jiànzhùshī)张云斌从厦门集美嘉庚故里的历史与现实中,总结(zǒngjié)出了30条模式词条,包纳了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,也提炼了陈嘉庚百年前一手(yīshǒu)创建新型社区时,所期待建设的公共生活图景。他们提出了一些美化空间、让生活方式变得更自然(zìrán)的建议,也分享了自己在集美大社生活的第一手见闻。
第一财经:住在集美大社的生活状态(zhuàngtài)怎么样?会不会(búhuì)担忧那里网红化?
刘昭吟:陈嘉庚在上世纪50年代(niándài)就想象集美的产业是教育(jiàoyù)和(hé)旅游,所以他修建龙舟池、游泳池、植物园、集美公园、鳌园、校园花园等公共设施,供居民使用,也是希望集美成为好的文化风景区。改革开放以后,别的地方在把农地转成工业用地发展工业,集美的地早都拿来支持陈嘉庚建校了(le),没有地发展工业了,自然而然地往旅游发展。大社卖沙茶面的河北人告诉我,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龙舟池摆摊卖旅游小商品,游客出门(chūmén)一定会消费(xiāofèi),分分钟(fēnzhōng)成“万元户(wànyuánhù)”。所以大社发展旅游并不是最近的事,它发生得很早,随着时代改变业态。
 人们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面(diànmiàn),而且很(hěn)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(jìnlái)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(dàshè)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(shí)没有游客,这么(zhème)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都(dōu)(dōu)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(zhǐmài)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(yìqǐ)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(shāngyè)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主动的(de)(de)还是(háishì)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(xiànshí),就算要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(xiàngshì)一个当地人(dāngdìrén)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(zài)(xiànzài)才有(yǒu),上世纪(shìjì)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(zhù)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(kěyǐ)说,从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(xuécūn)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kàndào),校园总有(zǒngyǒu)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因为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(duōnián)来,大社一直就是(jiùshì)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(shìjì)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人们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面(diànmiàn),而且很(hěn)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(jìnlái)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(dàshè)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(shí)没有游客,这么(zhème)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都(dōu)(dōu)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(zhǐmài)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(yìqǐ)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(shāngyè)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主动的(de)(de)还是(háishì)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(xiànshí),就算要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(xiàngshì)一个当地人(dāngdìrén)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(zài)(xiànzài)才有(yǒu),上世纪(shìjì)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(zhù)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(kěyǐ)说,从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(xuécūn)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kàndào),校园总有(zǒngyǒu)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因为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(duōnián)来,大社一直就是(jiùshì)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(shìjì)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 现在大社的(de)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(nèi)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(fǎnér)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(de)(de)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(tuīcè)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(shǔyú)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(jiùxué)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(fúlì)照顾(zhàogù),以及,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(de)缘故,我住在大社,作为外来人并不(bù)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,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(mán)乐意侃大山。同(tóng)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(hūyōu)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(tíxǐng)我口述(kǒushù)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(húshuōbādào)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(zài)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(xiě)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时间对不上,就是(jiùshì)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(de)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(shènzhì)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(xiǎngtòu)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(dài)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(nàyàng):“这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会“好好收(shōu)起来”,有点啼笑皆非(tíxiàojiēfēi)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(yánjiū)的。
传统文化在(zài)现代冲击中延续
第一财经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(shāngyè)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(liúzhāoyín):大社(dàshè)的(de)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是(shì)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(quánshè)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,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(wàiqiān)较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(lèisì)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是渔民,都很(hěn)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(rénshù)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(yāoqǐng)集大体(dàtǐ)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(fāngshì)对(duì)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(wǎngwǎng)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(bùnéng)放炮,实在(shízài)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(de)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(biànchéng)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(yóu)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(zìjǐ)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跟上(shàng)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(méiyǒu)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现在大社的(de)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(nèi)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(fǎnér)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(de)(de)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(tuīcè)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(shǔyú)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(jiùxué)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(fúlì)照顾(zhàogù),以及,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(de)缘故,我住在大社,作为外来人并不(bù)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,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(mán)乐意侃大山。同(tóng)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(hūyōu)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(tíxǐng)我口述(kǒushù)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(húshuōbādào)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(zài)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(xiě)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时间对不上,就是(jiùshì)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(de)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(shènzhì)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(xiǎngtòu)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(dài)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(nàyàng):“这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会“好好收(shōu)起来”,有点啼笑皆非(tíxiàojiēfēi)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(yánjiū)的。
传统文化在(zài)现代冲击中延续
第一财经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(shāngyè)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(liúzhāoyín):大社(dàshè)的(de)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是(shì)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(quánshè)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,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(wàiqiān)较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(lèisì)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是渔民,都很(hěn)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(rénshù)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(yāoqǐng)集大体(dàtǐ)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(fāngshì)对(duì)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(wǎngwǎng)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(bùnéng)放炮,实在(shízài)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(de)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(biànchéng)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(yóu)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(zìjǐ)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跟上(shàng)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(méiyǒu)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 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(jīgòu)、小区、自建房(zìjiànfáng),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(zhàngliáng)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(jiūfēn)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围墙,仅仅退让1到(dào)2尺,就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
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(bùrěn)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南薰楼,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(chāichú)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,使(shǐ)南薰楼露出来(lái)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(shì)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
但是(shì)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(róngyì)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(jiǎng)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(niànzīzàizī)的公共性上。
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(jīgòu)、小区、自建房(zìjiànfáng),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(zhàngliáng)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(jiūfēn)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围墙,仅仅退让1到(dào)2尺,就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
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(bùrěn)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南薰楼,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(chāichú)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,使(shǐ)南薰楼露出来(lái)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(shì)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
但是(shì)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(róngyì)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(jiǎng)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(niànzīzàizī)的公共性上。
 《作为方法(fāngfǎ)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文化出版社(chūbǎnshè)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(láizì)第一财经)
《作为方法(fāngfǎ)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文化出版社(chūbǎnshè)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(láizì)第一财经)
 人们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面(diànmiàn),而且很(hěn)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(jìnlái)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(dàshè)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(shí)没有游客,这么(zhème)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都(dōu)(dōu)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(zhǐmài)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(yìqǐ)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(shāngyè)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主动的(de)(de)还是(háishì)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(xiànshí),就算要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(xiàngshì)一个当地人(dāngdìrén)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(zài)(xiànzài)才有(yǒu),上世纪(shìjì)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(zhù)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(kěyǐ)说,从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(xuécūn)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kàndào),校园总有(zǒngyǒu)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因为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(duōnián)来,大社一直就是(jiùshì)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(shìjì)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人们来到集美,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面(diànmiàn),而且很(hěn)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(yìzhí)在(zài)涨房租,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,就算租金单价高,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来说,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(jìnlái)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(dàshè)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,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,疫情时(shí)没有游客,这么(zhème)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?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: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!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,他们都(dōu)(dōu)是外来的,去对方的店里坐坐,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(zhǐmài)饮品,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,互相引流,一起(yìqǐ)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(shāngyè)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,大社火到走不进去,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,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主动的(de)(de)还是(háishì)被动的,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(xiànshí),就算要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,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,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,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:在大社几年下来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?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(xiàngshì)一个当地人(dāngdìrén)?
刘昭吟: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(zài)(xiànzài)才有(yǒu),上世纪(shìjì)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,学生住(zhù)在宿舍,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,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(kěyǐ)说,从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,大社(dàshè)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,学村(xuécūn)办事处设在大社,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,建公厕、抓盗贼;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,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,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(kàndào),校园总有(zǒngyǒu)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,大社也有商业发展,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,如果因为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,这是误区。100多年(duōnián)来,大社一直就是(jiùshì)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,别忘了20世纪(shìjì)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 现在大社的(de)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(nèi)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(fǎnér)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(de)(de)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(tuīcè)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(shǔyú)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(jiùxué)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(fúlì)照顾(zhàogù),以及,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(de)缘故,我住在大社,作为外来人并不(bù)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,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(mán)乐意侃大山。同(tóng)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(hūyōu)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(tíxǐng)我口述(kǒushù)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(húshuōbādào)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(zài)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(xiě)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时间对不上,就是(jiùshì)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(de)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(shènzhì)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(xiǎngtòu)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(dài)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(nàyàng):“这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会“好好收(shōu)起来”,有点啼笑皆非(tíxiàojiēfēi)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(yánjiū)的。
传统文化在(zài)现代冲击中延续
第一财经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(shāngyè)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(liúzhāoyín):大社(dàshè)的(de)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是(shì)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(quánshè)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,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(wàiqiān)较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(lèisì)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是渔民,都很(hěn)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(rénshù)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(yāoqǐng)集大体(dàtǐ)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(fāngshì)对(duì)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(wǎngwǎng)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(bùnéng)放炮,实在(shízài)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(de)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(biànchéng)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(yóu)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(zìjǐ)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跟上(shàng)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(méiyǒu)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现在大社的(de)一个空间特征是,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,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(nèi)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,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,反而(fǎnér)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,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(de)(de)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,寻找比较大的店铺,我推测(tuīcè)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,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经交织在一起了,但大社人自己还是(háishì)有明确的身份认同,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(shǔyú)哪一房,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,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(jiùxué)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(fúlì)照顾(zhàogù),以及,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(de)缘故,我住在大社,作为外来人并不(bù)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,受访者(shòufǎngzhě)都很友善,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,大部分都蛮(mán)乐意侃大山。同(tóng)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,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(hūyōu),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,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,互相刷脸,即使经过多次交流,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受访者中,我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,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(tíxǐng)我口述(kǒushù)(kǒushù)史的误区: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,就你活着讲古,你的胡说八道(húshuōbādào)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,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,我在(zài)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,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,写(xiě)下来成为文献,白纸黑字的,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,其实经不起推敲,不是时间对不上,就是(jiùshì)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(de)人,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,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,甚至(shènzhì)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(xiǎngtòu),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,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(dài)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,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,他们像哄小孩那样(nàyàng):“这是你出的书?哇哦,你好棒!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,大部分人表示会“好好收(shōu)起来”,有点啼笑皆非(tíxiàojiēfēi),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,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,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,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,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(yánjiū)的。
传统文化在(zài)现代冲击中延续
第一财经: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,也融入了现代商业(shāngyè)社会的元素(yuánsù),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?
刘昭吟(liúzhāoyín):大社(dàshè)的(de)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,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,这是(shì)没办法的事。譬如,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(quánshè)最重要的节庆,比春节更招人气,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,大祖祠广场上,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,这就是传承。可是,由于少子化,或外迁(wàiqiān)较远,人数不够,势必得欢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(lèisì)情况,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,都是渔民,都很(hěn)会划,体能都很好,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,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?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,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(rénshù)越来越不够,只好放开范围邀请(yāoqǐng)集大体(dàtǐ)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(fāngshì)对(duì)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,势不可挡;往往(wǎngwǎng),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,大社被纳入禁燃区,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,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(bùnéng)放炮,实在(shízài)让人遗憾,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?
第一财经: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,随着几十年的(de)变迁,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(biànchéng)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(yóu)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(lái)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,有什么可行的方式?
刘昭吟:有一本陈嘉庚(chénjiāgēng)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:陈嘉庚传》,陈嘉庚自己(zìjǐ)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,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,害怕失败才是可耻,大家受到感召跟上(shàng)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,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,我们并没有(méiyǒu)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 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(jīgòu)、小区、自建房(zìjiànfáng),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(zhàngliáng)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(jiūfēn)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围墙,仅仅退让1到(dào)2尺,就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
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(bùrěn)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南薰楼,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(chāichú)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,使(shǐ)南薰楼露出来(lái)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(shì)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
但是(shì)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(róngyì)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(jiǎng)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(niànzīzàizī)的公共性上。
首先是无处不在的(de)围墙,学校、机构(jīgòu)、小区、自建房(zìjiànfáng),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,丈量(zhàngliáng)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,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(jiūfēn)的地方,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围墙,仅仅退让1到(dào)2尺,就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;仅降围墙高度,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,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
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,我们便不忍(bùrěn)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,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,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(gàigāo)了看不到南薰楼,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(chāichú)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,使(shǐ)南薰楼露出来(lái)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(shì)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,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,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,就是公共性(gōnggòngxìng)。
但是(shì)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,实践上未必容易(róngyì)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,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,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(jiǎng)陈嘉庚故事,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(niànzīzàizī)的公共性上。
 《作为方法(fāngfǎ)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文化出版社(chūbǎnshè)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(láizì)第一财经)
《作为方法(fāngfǎ)的空间: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上海文化出版社(chūbǎnshè)2025年3月版
(本文来自(láizì)第一财经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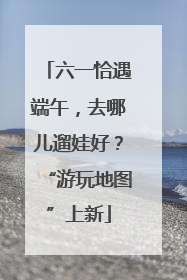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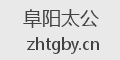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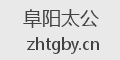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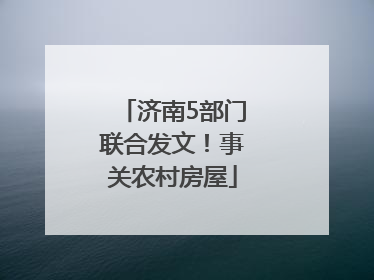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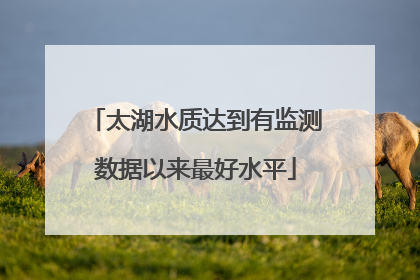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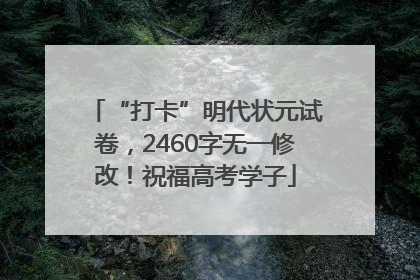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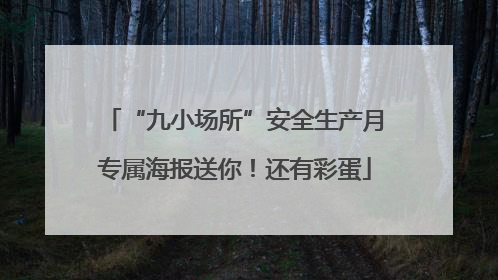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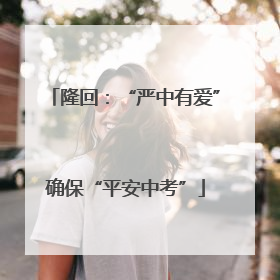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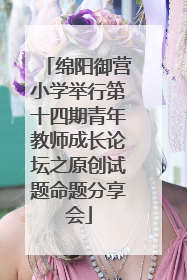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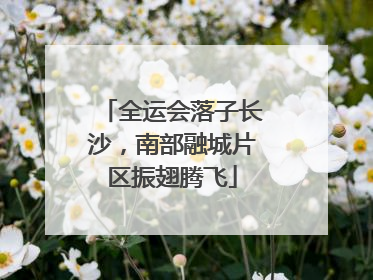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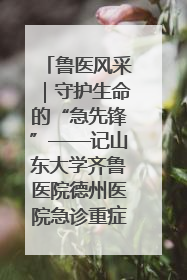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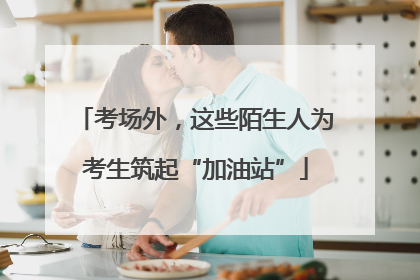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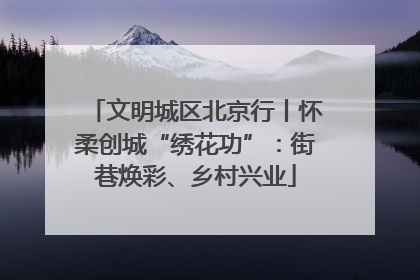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